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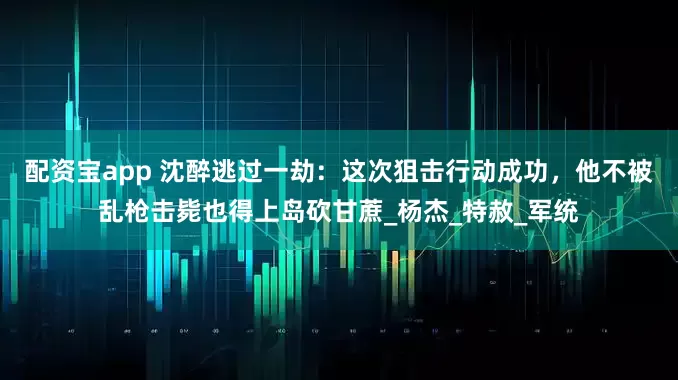
《头条文章养成计划:细解七批特赦战犯名单中的现象》
通过细致分析七批特赦战犯的名单,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大多数军队中的将军级特务,几乎都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获得了特赦,而在此之前,仅有几位军统及保密局的高级人员获得了特赦。他们分别是:曾任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、游击司令沈醉,军统电讯处副处长、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,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,以及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,这些人在1960年至1966年期间陆续被特赦。
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,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半数的军统(保密局)和中统(党通局、内调局)的省站站长。这些人的名字大多耳熟能详:例如周养浩(《红岩》中的沈养斋),陈旭东(曾任东北区副区长,类似《渗透》中的陈明),以及文强(曾任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,“徐州剿总”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)等,他们都在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与沈醉、周养浩并称“军统三剑客”的徐远举,在1973年1月22日已经因病去世,而他身后还有十三四个将军级的特务同行。值得一提的是,军统(保密局)在撤销前,每年都会召开一次“四一大会”,然而这些大会上,真正能见到的省站站长寥寥无几。像文强、吴景中这样的资深特务,几乎从未参加过大会,因为他们或者由于之前的原因无法参加,或者因为自己地位较高,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场合。
展开剩余78%1949年,老蒋带着毛人凤逃往台湾,各省的站长们多数被抛下,表面上是“潜伏”,实则已成为“弃子”。唯一的例外是吴景中(《潜伏》中的吴敬中),他毫不顾忌毛人凤的严令,冒险乘坐飞机逃离了即将被合围的天津。
沈醉在曾担任过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之后,曾在昆明掌控逃离机票,但由于害怕毛人凤的报复,他一直未敢离开。最后,在昆明起义通电后,他和西南特区的几位特务,包括徐远举、周养浩等,成为了同仇敌忾的“难兄难弟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,沈醉是所有将军级特务中最早获得特赦的,这并非是因为他在云南起义通电时签字(事实上,他是在压力下签字的),而是因为他后来的立场较为特殊。他与李弥、余程万等人成为了“七兄弟”,决定与卢汉对抗到底,最终被关进云南陆军监狱。与沈醉不同的是,许多其他的大区区长和省站站长,因其身上的血债太重,最终被放到了最后一批特赦的名单中。
沈醉回忆录中提到,像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些人的罪行几乎无法原谅:“他们是重庆大屠杀、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。即使我参加了起义,放他们走,也很难交代。”这些曾亲自参与暴行的特务被捕后,意识到了自己深重的罪孽,甚至在被囚禁在白公馆时,听到烈士墓前群众的激愤呼声时,都被吓得面色苍白、心惊胆战。徐远举更是在这种情形下,不时用袖子擦去因为惊恐而流出的冷汗。
按理说,像徐远举和周养浩这样的角色,早该被处以死刑。然而,到了战犯管理所,他们虽然享受了一些优待,但如果提前获得特赦,烈士们的亲友显然不会接受。沈醉之所以能提前获得特赦,主要是因为他的经历较为特殊,而他所在的“技术型”职位,如董益三等人,在军统时期更多涉及技术工作,与血腥暴行的关联较少。
沈醉的背景也与他的其他同僚有很大不同。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任职前,他一直从事交通员、稽查处长等较少直接与地下党对抗的工作,血债较少。直到最后,他执行的三次重大刺杀任务均以失败告终,这一反常现象对他来说,实则是一种“塞翁失马”的命运转折。
其中,沈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刺杀任务,便是针对原陆大校长杨杰的暗杀行动。1949年8月,沈醉接到毛人凤发来的“亲译密电”,命令他立即在昆明刺杀杨杰等五人。尽管沈醉心惊胆战,但他依然决定按命令行事。初步策划包括在杨杰的回家途中用无声手枪射杀,或者如果杨杰未出门,则直接在其住所进行刺杀。
沈醉与杨杰曾有过接触,杨杰不仅是沈醉家庭的熟人,而且两人关系较为亲近,经常一起聚会,沈醉的孩子们也很喜欢杨杰。为了制造出不被察觉的接触机会,沈醉特意选择在杨杰夜间返回时进行行动。然而,他的计划在细节处出现了破绽:在一次行动筹划时,沈醉的母亲恰巧在旁,察觉到异常并大发雷霆。沈母严厉责骂他,指出若他真动手刺杀杨杰,未来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,都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。最终,沈醉在母亲的压力下,放弃了这一刺杀计划。
沈醉的这一转变,也从某种程度上让他逃过了一场血债,杨杰最后在香港被叶翔之所杀,而沈醉则没有进一步的牵连。这一段历史,也让人不得不感叹,如果没有沈母的干预,沈醉的命运或许会有极大的不同。
在这之后,沈醉无论如何行动,都注定难以逃脱毛人凤的打压。即便他如吴景中般能够弃职出逃,他依旧面临着不容乐观的结局,因为他并没有吴景中那样的“庇护网络”。如果沈醉最终逃脱,他的命运可能是过早地消逝在岛上的寒风之中。
发布于:天津市翔云优配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